高明勇:寻找与故乡的“连接点”
一个人,如果一直呆在故乡,无所谓思念不思念,故乡就是日常,日常的往往也是最容易习焉不察,最容易无视和忽视的。
一个人,一旦离开了故土,远离了乡音,并且年岁日增,漂泊感越强,对故乡的思念才会更加醇厚,不管是否愿意承认,他都会有意无意地寻找与故乡的“连接点”。
这段话,是我在和一位故友的一次交流时,随手记下的话。
寻 找 与 故 乡 的 “连 接 点”
文丨高明勇(政邦智库理事长)
作为一个资深爱书人,漂泊在故乡之外二十多年,客居北京也有十四五年光景。疫情之前,每次春节返乡,我总会不自觉地,在随身的行李中,塞几本带有乡村体温的书。记得带过程章灿老师的《旧时燕——一座城市的传奇》,带过莫砺锋老师的《浮生琐忆》,带过梁鸿的《中国在梁庄》,带过熊培云的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,带过十年砍柴的《进城走了十八年》,带过潘采夫的《十字街骑士》,带过阎连科的《我与父辈》,带过郑大华的《民国乡村建设运动》,带过李景汉的《定县社会概况调查》,包括一些民间的村史或家谱,试图以熟悉的陌生人视角,重新打量自己若干年前生活过的地方。
每次总有新看法,但每次也总有叹息,故乡注定是我们的一种“人生病”,每次匆匆记录的点点滴滴,仿若为这种病的病历又写下了几行。有时说“老家”,有时说“家乡”,有时说“家里”,有时说“故土”,但写作时,我还是习惯于写为“故乡”。
前些年,父亲刚退休后,我一直鼓励他写点回忆性的文字,以私人记录的形式观照这些年的大时代变革,虽然他几乎没发表过文字,这样的文字哪怕只有“家庭史”的记忆色彩,依然有非凡的价值。
我对梁启超、胡适所倡导的承接“自传”的传统素来推崇,自己也有所践行,潜意识对别人的传记也更为关注。就我个人而言,从小在农村长大,伴随着饥饿的童年回忆,包括亲人的叮嘱在内,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“进城”,摆脱农活,逃离农村,远离农民,告别农业——这几乎都是所有农村青年的梦想。就像路遥笔下《平凡的世界》中的孙少平,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,进城的梦想是相似的,不同的梦想路径又有不同的人生苦痛。这个角度说,独特的个人记忆,与这个国度的共同记忆之间又形成了某种张力和呼应。
所以,在故乡、阅读与个人史之间寻找与故乡的“连接点”,又是一番滋味。学者陈平原在新作《故乡潮州》中,开篇就是《如何谈论“故乡”》,将故乡细分为乡音、乡土、乡愁与乡情,他认为,谈论乡土,最好兼及理智与感情,超越“谁不说俺家乡好”,拒绝片面的褒扬与贬抑,在自信与自省之间,保持必要的张力。
就近年的私人阅读史,我择取四位老友的四本书,作为四个与故乡的“连接点”,作为打开故乡的四种方式。
春读“乡史”,宜读“学者之文”,如熊培云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,研究中国,从“打捞乡村”开始;
夏读“乡恋”,宜读“评论家之文”,如伍里川《河流与柴火》,柴火堆积成垛,乡愁逆流成河;
秋读“乡亲”,宜读“作家之文”,如韩浩月《世间的陀螺》,为故乡的亲人立传;
冬读“乡思”,宜读“思想家之文”,如陈平原《故乡潮州》,在洋铁岭下,风景的再现。

一、春读“乡史”:研究中国,从“打捞乡村”开始
平素读书,我喜欢两种方法:其一,纵向阅读,搜集同一作者的相关作品,从其“书写史”的角度出发;其二,横向阅读,搜集同一主题的相关书籍,从己“阅读史”的角度出发。
读熊培云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时,我专门从书架上抽出新旧几本书:莫言的《我的高密》、北岛的《城门开》、曹锦清的《如何研究中国》和郑大华的《民国乡村建设运动》。同时还回顾熊培云的“书写史”。他的目光从“国”(《思想国》)到“社会”(《重新发现社会》)再到“村庄”(《一个村庄里的中国》),从宏观走向微观,从抽象走向具体,从星空走向土地,笔触从灵魂到灵魂居所。
纵横交叉的阅读之旅,既有联想之魅,也不无跳跃之美。
北岛在《城门开》中说:“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,重建我的北京——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。”熊培云则是在用文字重建一个乡村,重建他的小堡村——用他的小堡村否定如今的小堡村。
熊培云说,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,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。这本书或许意味着,他仍在“天堂”与“故乡”之间游荡。
他认为最真实最值得信赖的历史,不是在政治广场上的振臂一呼,不是某个主义的从此流行,不是一场血腥战争的名字,而是无数具体的小人物的具体命运。我所理解的,他是在提出一个“如何研究中国”的实验文本。
因此,对熊培云提出的“保卫乡村”,我认为“打捞乡村”更妥帖。虽然数年前被提出的“底层沦陷”不无悲怆之感,但“记忆遗忘”或许更让人痛心。“保卫”是指面临改变,而“打捞”是指已然改变,熊培云的“乡村之旅”,我更愿意称为“打捞乡村”的公民自觉行动。
那么,熊培云历时十年打捞出了什么?
或许,印象深刻的是他故乡的“方尖碑”——两棵古树,一棵是立于村南晒场上的被人拐卖的古树,一棵是自家被伐走的枣树;以及重返故乡时他发现,他和同龄农村青年相似的刻骨铭心的童年,和史无记载、坊无流传的“布水寺大屠杀”。
当然,被“打捞”出来的,远不止这些,熊培云的“雄心”是“打捞”一个村庄里的中国,关注具体人的命运,认识脚下的土地,“谋求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国家的改变”。
恒心比雄心更重要。所以,可以看到,他从容地讲解着另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中国。在这里,有董时进,曾上书反对土改政策,组建中国农民党,被遗忘的“中国三农问题第一人”;有被称为“狗日的户口”的户籍戒严政策的前世今生;有影响一时的关于农民“李四喜思想”的大讨论;有在“真理大讨论”之前两年撰写过《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》而被残忍杀害的赣南学生李九莲;有渐行渐远渐无影的近百年前高级知识分子晏阳初、梁漱溟、李景汉、陶行知等人“捧着一颗心来”的“回到农村”运动;有当年“日本佬”如蝗虫过境的民间叙事。
费孝通曾感叹,“关注社会生态,而没有重点去关注社会心态”。我相信熊培云是明晓这一感喟的,因为在进入他构建的村庄史后,才发现,他“打捞”出更多的我们或许已熟悉而陌生的“追问”:城乡不平等的起源何在?无权无势者如何抵抗?为什么要有乡镇精神?地方如何记忆?
如莫言所说,放眼世界文学史,大凡有独特风格的作家,都有自己的一个“文学共和国”。
小堡村之于熊培云,不仅是“敝帚自珍”,更是在“诠释时代”。从“小堡村史”,到“中国乡村史”,再到“中国社会心态史”,从三个层面对乡村进行“打捞”。他所谓的写作方法层面的“三通主义”(事件上打通,地理上打通,理性和感性打通),其实就是一种“打捞”,超越时空隧道,超越乡村羁绊,探求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,寻找真确的答案。
十年砍柴说,《进城走了十八年》,或许这个时间足以达到目的地,而“回家”,却需一生的时光,都未必能抵达 。
我们时而“身在异乡为异客”,时而“身在故乡为异客”,在“异乡”与“故乡”之间游荡。
春天,万物萌发,老树新芽,适合读“乡史”,寻觅遗失在白字黑字,打捞散落在田野草莽,考证掺杂在野史笔记,捡拾在残垣断壁的乡村记忆。
二、夏读“乡恋”:柴火堆积成垛,乡愁逆流成河
至若夏日,绚烂夺目,适合读“乡恋”,而评论家的书写,往往让人触感到炽热情感背后的一丝坚硬与冰冷。
每个人心中,都有一个故乡。或存在于念念于兹的真实世界,或存在于切切于心的精神空间。
有的人看重物理意义的故乡,故土难离,故人难分,故事难忘,即便年少轻狂背井离乡,终愿落叶归根。有的人看重精神意义的故乡,故乡是心灵的城堡,故乡是灵魂的图腾,故乡是精神的家园,更多时候,故乡是一团化不开的情愫,只存活在记忆与想象之中。
浮云游子意,落日故人情。

夏日读伍里川的“非虚构写作”《河流与柴火》,一丝凉意,一丝暖流:游子归来,少年不再,痴心却难改。身在故乡,常思异乡,此情如浮云。
一度,河流与柴火是生活的日常之物,十分普遍,河流更多生南方,柴火更多长北国。时下,河流多有干涸,柴火亦不多见。
文学角度观之,“河流”是文学的意象,“柴火”是生活的象征。《河流与柴火》封面选自伍里川自拍摄影作品,柴火散落于河流之上,冷峻色调,略显悲凉。
伍里川,是一个像河流名字的笔名,本名刘方志,另有笔名费十年。
伍里川,取名于“五里川”,是一个地名,位于河南五里川镇,五里川河,五里川盆地,更重要的是,这是伍里川的生命版图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标。
伍里川,南京江宁人。少小入行伍,转业返故乡,报业十数载,时有杂文名。他没有读过大学,曾在军营十年,期待走上文字之路。
伍里川,写诗歌,字里行间按耐不住诗性;喜篆刻,如匠人般终日把玩;爱踢球,常奔跑于绿茵赛场;尤善评论,一手写辛辣时评,世间百态皆入笔端,一手写隽永杂文,喜笑怒骂都可成篇。
军旅生涯对他影响至深。走路挺胸收腹,虎虎生风,说话快言快语,正直爽快。
文如其人,其文干脆利落,简洁有力:无八股文风之端庄规整,无学院为文之书袋痕迹,文字更多是从生活中炼出的,有命运跃宕的磨练,有生活多艰的锤炼,有文字驾驭的修炼,有人生况味的提炼。笔名费十年,可见一斑:费力奔波十年,常感浪费十年。
江宁是刘方志物理意义的故乡,精神意义的故乡在河南那个叫“五里川”的地方,那里寄存着他的青春、梦想与情感。一本写故乡故土故人故事的非虚构散文集,署名用的是异乡飘荡的地名,耐人寻味。
评论家伍里川笔下的故乡叙事,是一个个鲜活的细节,细节背后隐藏着的是他极为克制的问题意识:《消失的村庄》、《愤怒的柴火和无地自“容”的故乡》、《村史达人》、《村庄之死》、《你我的故乡,都不会再来》……从标题可以想见一位游子归来对故乡的失落与迷失的锥心之痛。但这种痛,并非直接以“愤怒”面世,就像听我韶韶的主持人吴晓平在序言中所说,伍里川学会了“武侠高手的绵里藏针”。
《和一棵树永别》,写的是自己家里的一棵腊梅树,因拆迁而出卖,因出卖而悔恨,虽有“她凭啥要被我们出卖”的困惑,却“我竟然没有在永别的边缘,拉她一把。这终究会令我抱憾终身。”
以游子之心看故乡,乡愁是游子的避风港,以评论之笔写故乡,故乡是评论的古战场,即以挑剔的眼光反思故乡,以初恋的炽热拥抱故乡。
正如托马斯·沃尔夫所说:“认识自己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;寻找到故乡的办法,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,到自己的头脑中、自己的记忆中、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找它。”
抑或,在伍里川“非虚构”的文学世界里,柴火堆积成垛,炊烟袅袅于四合;乡愁逆流成河,悲欢杳杳已成歌。
三、秋读“乡亲”:为故乡的亲人立传
秋天,常常想起儿时在故乡参与秋收的场景,故乡的亲人们起早贪黑,来去匆匆,只为多收三五斗。然,人如蝼蚁,命若秕谷,时光荏苒,不过一二十年光景,物是人非,当用作家敏感的笔触去记录他们的点点滴滴时,他/她们的形象才能“立”起来。
2018年冬天,我和弟弟分别从外地回到故乡,参加外婆的葬礼。来去匆匆,葬礼当天上午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空档,就想着回我们自己的村子里看看荒废了几年的老宅。
路途倒不远,不过五六公里,只是刚刚落雪,四下雾气,自然无法坐车,就决定徒步。带着乡亲们不解的眼光,在雪地里一个多小时的小心翼翼,两个“冰花男孩”竟然在村子前面的麦地里迷路了。
这让我们弟兄两个都很沮丧,尽管天公不作美,不容易辨识道路,但这毕竟是我们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故乡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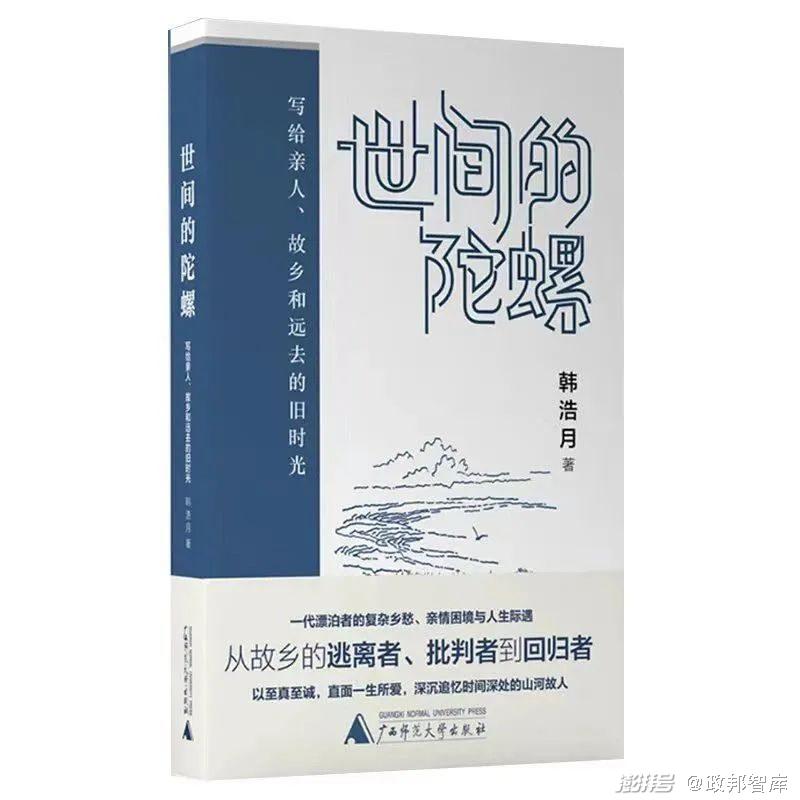
在故乡的麦田里迷路,应该是漂泊一代的真实隐喻——对于故乡而言,漂泊者是熟悉的陌生人。

当时,收到韩浩月“写给亲人、故乡和远去的旧时光”的《世间的陀螺》,读完我有点重新认识韩浩月的感觉。
正如赠语所写:“故乡是杯烈酒,不能一饮而尽。”他写“去看油菜花的父亲”,写“远方的母亲”,写“被坏话包围的爷爷”,写“传奇的六叔”……不管写谁,这些“一生所爱的山河故人”,都让人走进了一位作者的隐秘世界,哦,原来,你所熟悉的朋友曾这样生活着。尤其是,他对生命细节的记录,对生命记忆的执着,对生命关系的真诚,都让人感动。
长期以来,浩月在公众视野中给大家的形象,是影评家,时评家,情感专栏作者,这本“故乡书”,则更多是以作家的名义对故乡生命印记的观察。
客观讲,读这本《世间的陀螺》,我甚至有些羡慕的成分。为故乡的亲人立传,一直是我想做而未来得及做的事情,和浩月比,除了才情与勤奋,我可能还差一个叫做“灵子”的编辑。
漂泊者与故乡的纽带,其实是很微妙的。亲人在时,故乡是春节;亲人去后,故乡是清明。纽带的中枢,是“亲人”。可是,这些故乡故人,生命如此脆弱,也是如此容易遗忘。
有一段时间,我曾和父亲一起追溯家谱,重新编写,想借此了解家族的起源与传承,身边亲人在这个家族谱系上的节点;再往前推,我曾对村史写作现象持续关注,一个村庄的生长史,承载了太多的恩怨情仇,喜怒哀乐,和个体与家庭的命运跌宕。
其实,对于游子来说,打开故乡有很多种方式。
比如,我所喜欢的同乡作家阎连科,他在《北京,最后的纪念》中,记录“一把铁锨的命运”,“一张锄的新生命”,观察“一畦芹菜的生长史”,“一棵丝瓜的前缘今生”,“榆树下的小白菜”,追忆“一棵失去的槐树”,“一条找不到家的土著狗”,篇篇写的都是自己漂泊的异乡风物,可是字里行间全都是游子对无法排解的乡愁的念叨。
比如熊培云,透过“一个村庄里的中国”,你能看到这些年一个国家的前行巨轮,在一个小小村落里的零落车辙。
比如作家梁鸿,作为文学研究者,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,又用文学的笔触写出了梁庄里的中国,和走出梁庄的中国。
还有老友伍里川,作为出走多年的游子,在故乡“一本写故乡故土故人故事的非虚构散文集,署名用的是异乡飘荡的地名,耐人寻味。”
如果我来写故乡,我会选择为故乡的亲人立传。就像浩月这本书的推广语:“一代漂泊者的复杂乡愁、亲情困境与人生际遇,从故乡的逃离者、批判者到回归者,以至真至诚,直面一生所爱,深沉追忆时间深处的山河故人。”
我的写作素材库里,收藏了不少关于亲人的追忆材料和特定意象。
关于奶奶,有“三个干桔子”的故事,关于大姑、大姑父,有六封信的追念。还有执拗如牛又憨厚真诚的二姑父,嗜烟如命但待人亲善的三姑父,善良一生的二姑、三姑、四姑……在故乡,除了亲人,似乎没有谁还记得,即便是亲人,很多时候,除了名字和生命中的点滴,也没有什么会被铭记。我的写作计划中,一直想写一本书,书名是《麦田里的教育》,向父亲以及父辈致敬,是的,从小到大,所有的家教,所有的童年,所有的动力,几乎都来自麦田。
正如诗人海子在《麦地》里写道:“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,收麦这天我和仇人,握手言和,我们一起干完活,合上眼睛,命中注定的一切,此刻我们心满意足地接受。”和笔下故乡的亲人一样,我们都是“世间的陀螺”。
四、冬读“乡思”:在洋铁岭下,风景的发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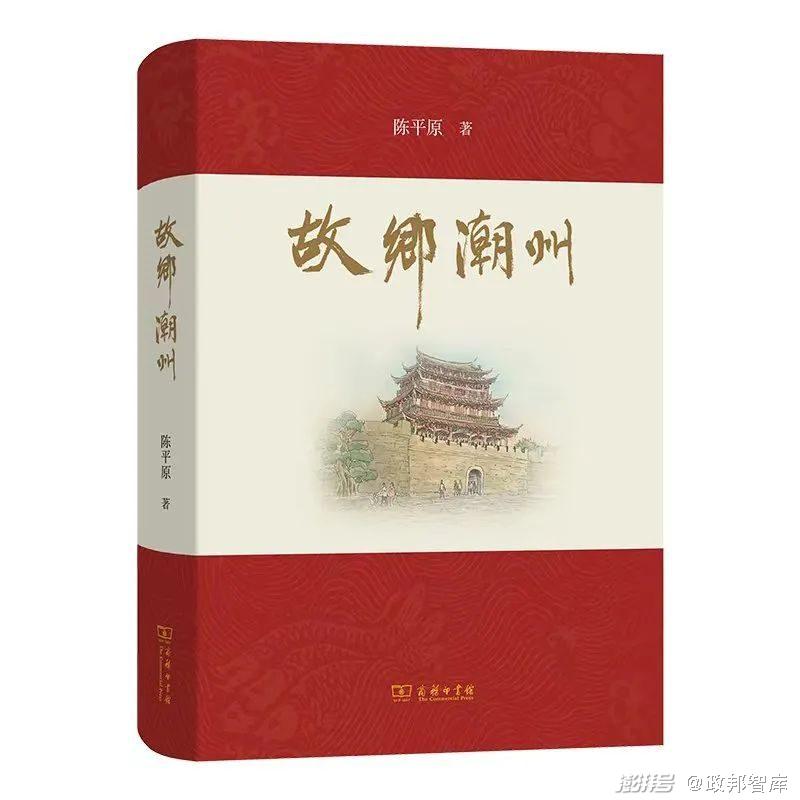
冬天的北京,天寒地冻,风硬如刀。游子与故乡之间的藕断丝连,更是在故乡与异乡的时空转换中杂糅,就像冬日打在屋檐下墙壁上那一缕阳光,穿过历经风雪的枝枝杈杈,挤过那苦寒透骨的冷风,仍有暖意在心头。

此时打开陈平原先生的《故乡潮州》,不由地陷入深思——他不仅“六看家乡潮汕”,还思考“如何谈论‘故乡’”,不仅记录“洋铁岭下”的“在家生活”,还主持梳理“故乡人文”的《潮汕文化读本》。
之前,我曾邀请陈平原先生参与一期“政邦茶座”,我说看他很喜欢周作人的一句话: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,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。”(《故乡的野菜》)这句话很容易联想到苏轼的一句词:“试问岭南应不好。却道。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
我问他,北京和潮州,哪个更容易让自己“心安”,或者说,是不同年龄阶段的“心安处”?
陈平原先生回答说,为家乡潮州写一本书,这念头是最近五六年才有的。这一选择,无关才学,很大程度是年龄及心境决定的。年轻时老想往外面走,急匆匆赶路,偶尔回头,更多关注的是家人而非乡土。到了某个点,亲情、乡土、学问这三条线交叉重叠,这才开始有点特殊感觉。
对他来说,这个时候谈论“故乡”,既是心境,也是学问。具体说来,在一个虚拟世界越来越发达、越来越玄幻的时代,谈论“在地”且有“实感”的故乡,不纯粹是怀旧,更包含一种文化理想与生活趣味。
值得注意的一点,年轻时,作为北京大学教授,陈平原倡议成立“北京学”;在退休的年龄和心境,他被聘为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,着力推动“潮州学”/“潮学”。
曾有论者指出,理想化的知识分子生活,应该是少年赋诗,中年治学,晚年修志。且不论合理与否,至少这也是从一些主要知识分子的经历中“提炼”出来的。从“北京学”到“潮州学”,正是从“异乡”到“故乡”的心路历程的投射。
或许正是因为,“眼皮底下的日常生活,以及那些蕴含着历史、文化与精神的习俗,因习焉不察,容易被忽视”,陈平原才致力于构建一个“纸上的潮汕”,这也是在“压在纸背的心情”之外,呈现出“铺在纸面的思索”。
他在《如何谈论“故乡”》一文中说:“我儿时生活在汕头农校,那是在洋铁岭下,在少年的我看来,潮州就是了不起的城市了。只要是远走他乡,即便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,也都会有乡愁。”
洋铁岭下,不仅保存着他儿时的记忆,也是“千古文人侠客梦”的出发地。在这里,“风景的发现”——即何人、何时、何地、因何缘故发现此处“风景殊佳”,绝对是一门学问。在理智与感情、自信与自省的权衡之后,陈平原的落脚点不无“建设性”,兼具“国际视野”与“故乡情怀”:如何突破小潮州的格局,从大潮汕的角度思考与表达。
作为思想家,陈平原与故乡的“连接点”,则是如何“认识脚下的土地”,在洋铁岭下,“风景的发现”,发现儿时遗忘的风景,发现今天变化的风景,发现未来潜在的风景。并旨在希望这些“发现”在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人身上,能传承下去,不断丰富这些风景。
关注故乡,在不同的季节时间,有不同的书写方法,也有着不同的打开方式,每一种方式,都是在寻找与故乡的“连接点”。
参考资料:
《研究中国,从“打捞乡村”开始》,高明勇,《中国青年报》,2011年12月27日
《进城虽久,难忘乡村》,高明勇,冰川思想库,2017年1月 31日
《柴火堆积成垛,乡愁逆流成河——读伍里川<河流与柴火》>,高明勇,《松原日报》,2020年4月1日
《为故乡的亲人立传|读韩浩月<世间的陀螺>》,高明勇,凤凰网文化频道,2019年7月4日

